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这一面,是鲜为人知的教授坂本龙一
想想当时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

和大卫·鲍伊主演[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又傲娇地和大岛渚导演说“你让我配乐我才来演”。
于是,除了出演,还就这样谱出了在世界范围广为传唱的经典神曲《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后来的[末代皇帝]配乐又不小心拿奥斯卡,从此和贝托鲁奇、阿莫多瓦等大导演合作了不少经典配乐。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早前在北影节放映时,有一票难求之势,因为影迷、乐迷们都是冲着他的名字而来:
坂本龙一,一个传奇的名字,而我们亲切地叫他“教授”。

“教授”的称呼,其实来自早期他在乐队YMO时高桥幸宏的一句打趣,“东京艺大研究生哎,妥妥以后的教授。”
影迷们熟悉教授后来出演电影和配乐的那些经历,对其中的趣事如数家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教授的音乐事业其实是从玩电子乐开始的。
1978年,26岁的教授和同样年轻气盛的细野晴臣、高桥幸宏一起组成了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黄色魔术交响乐团)。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开创新的世界电子乐史。

《坂本龙一:终曲》中有一段珍贵的早期影像,3人在舞台上表演《东风》,教授接受采访展现电子合成器制作音乐的优势。
是时候把古典优雅的教授形象先放边边了,我们教授年轻时,也是个前卫酷boy。

YMO的结成,要起源于1977年的三个闲人。
闲人一教授,研究生刚刚毕业,可他讨厌上班。教授在自传里说,其实当时上研究生也是为了逃避上班。
反正,这时他的生活就是整日游走在东京大大小小的录音室里,给人家打打零工,赚一点生活费。
教授从小到大学,一直学的是古典音乐,他喜欢的是德彪西那一类,还很少接触到流行乐和民族乐。

直到毕业后东跑西颠打零工的过程,结识了一圈剧团艺术家和现代音乐人,这其中,就有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是70年代最重要的音乐人之一,也是深受披头士、沙滩男孩等六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影响成长起来的那一代。
正是在山下达郎的推荐介绍下,教授和另两个闲人相遇了。
闲人二细野晴臣,玩的不知第几个乐队Tin Pan Alley正在解散边缘,细野正边思考人生边寻觅下一个团队成员。
细野的音乐生涯其实比教授开始的早很多,69年他在大学时就加入了一个名为Apryl Fool的迷幻摇滚乐团担任贝斯手。
但他更重要的经历,显然是之后和铃木茂、大泷咏一等人组成的Happy End乐队(はっぴいえんど,1969-1972)。

Happy End算得上是日本自家摇滚乐的起始点,他们是第一支用日语唱摇滚的乐队,那张经典的《風街ろまん》在日版《滚石》评选的影响日本百盘中无可争议的排名首位。
但Happy End很短命,没过三年就解散了,细野后来也是尝试玩了各种音乐风格,到YMO时,流行性和实验性并存的部分,很大程度就是细野的功劳。
闲人三高桥幸宏,高桥也是早早就开始了乐队生涯。
最早是在民谣团体GARO中当鼓手,后来,又加入了70年代中期风头一时无两的重量级乐队 Sadistic Mika Band(虐待狂米卡)。
再然后是和今井裕、后藤次利等人组成的Sadistic,到和教授相遇时,乐队也已在解散档口了。

有趣的是,高桥除了是鼓手和歌手,还是个服装设计师,一手包揽了后来YMO的形象和造型设计,也带着我们教授这个土直男开始变潮起来。
而且高桥和细野从小就是朋友,这下再带上了教授一起玩。
一次细野邀请两人去家里吃饭,这之后就打开了一册笔记本,上面画着富士山爆发的样子,写了几个大字:400万张。
“把Martin Denny的《Fire Crackecr’racker》用合成器以电子曲风重新编曲,就能在世界卖出400万张。”
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YMO结成了。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经济腾飞、科技发展,对于刚刚从战争阴影走出来的日本人来说,一切都是梦幻又极具未来感的。
和日本有些同病相怜的德国也是。
战后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涌现了一批用音乐来推翻重建的前卫摇滚乐队:
Kraftwerk(发电站)、Can(罐头)、Faust(浮士德)等等。
他们使用电吉他,使用电子合成器,用预先录制好的磁带录音来创作音乐或是制造某种音效,音乐中融合了电子、实验、迷幻和先锋。
而Kraftwerk显然走的更远,他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原声乐器,只用70年才刚刚出现的便携合成器Minimoog来制作他们的“机器人音乐”。

而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成功,首专《Autobahn》即冲上了美国流行音乐专辑排行榜前位且高居不下。
电子音乐由此迅速开始进入到流行音乐领域。
德国的Kraftwerk,显然成了教授、细野三人YMO的模仿目标。
其实,早在大学时代,教授就多少感知到了当代音乐的发展局限,他曾断言说:
西洋音乐已经到了尽头,未来属于电子乐和民族乐。
细野、高桥虽然不是像教授这样接受严格的音乐教育和训练而来,但他们在多年乐队生涯中摸爬滚打、自学成才,而且更练就了对流行音乐的敏锐嗅觉。
一种渴望用电子乐向世界展现黄种人音乐的想法,在三人脑中渐渐成型:
不是脱胎于古典乐的白人音乐(即White Magic),也不是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即Black Magic)——而就是“Yellow Magic”。

虽然是受Kraftwerk启发,但并不走Kraftwerk那样强调未来机械感、冰冷感的“机器人”风格。
而是在电子乐中,加入日本民族风情,甚至中国地方小调,亚洲文化里的明媚、柔和、多元,组成了特有的YMO风格。
在形象设计上,教授在高校时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的经历又给了他们意外的灵感。
高桥把很多“红色中国”的元素,运用到了乐队的形象设计上。
比如他们最著名一张专辑的封面,是穿着红色西服的三人和模特围坐成一桌,以一种近未来的科技感和复古的诡异感的混合体,面向观众。

他们唱《中国女La Femme Chinoise》(灵感来自戈达尔的[中国姑娘]),他们从中国小调《让我们荡起双桨》取材歌唱《东风》。
将68一代新青年的红色幻想杂糅和融入进电子合成器的音色狂欢中。

78年11月,当YMO发布第一张专辑时,并没能像Kraftwerk那样一战成名。
但意外机缘是,当时前来日本寻找合作的美国公司A&M Record留意到了这张专辑。
于是,第二年,他们即发行了美版专辑,并策划了美国巡演。
说YMO是在美国成名的并不算夸张,他们从给人暖场到自己演出,很快就积聚起了大量听众。
在舞台上也仍然是那一副打扮,三人穿着红色中山装,在舞台摆弄着先进而新奇的合成器,唱的却是东方音乐,真人寡言沉默,故意与观众保持了距离。
即使是互动,也是通过声码器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到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发售,他们很快就登上了流行音乐榜,几首代表作《Rydeen》、《Behind The Mask》更是广为流传。
就像当初的豪言,三人真正把“黄色魔法”风潮带到了世界各地。
火到甚至就连迈克尔·杰克逊都翻唱了他们的名曲《Behind The Mask》。而这股风潮又一路从美国回到了日本,他们一跃成为日本当时最著名的乐队,很快在武道馆座无虚席。
更重要的是,以二专《Solid State Survivor》为代表的Synth-Pop(合成器流行,日本叫Techno-pop)风格,使得这一时期的YMO成为了电子乐的先驱之一。
YMO只存在了5年,从78年结成到83年解散,但他们的影响却在后来的电子乐和摇滚乐中无处不在。
他们对合成器的使用、先进的采样手法、和各种风格的融合,大大拓宽和启发了后来的电子音乐人们。
80年代的底特律音乐人们,就是在听着Kraftwerk和YMO的音乐中,搞出了更具有未来主义的Techno音乐。
也是缘于78年YMO的结成,以及Kraftwerk四专《The Man Machine》的发布,78年因此也被电子乐迷们称为“Techno元年”。
而YMO对英国新浪漫(New-romantic)的影响就更不言自明,70年代末以Japan乐队为代表的新浪漫乐队,本来就和YMO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Japan的主唱David Sylvian和教授坂本龙一也成为一生的好友,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还合唱了那首著名的《禁色》。
在电子音乐史上,尤其是亚洲的电子音乐史上,YMO绝对算得上是革新的先锋和电子流行化的鼻祖。
想想当时细野邀请教授加入YMO时,教授还曾一脸不情愿地婉拒,幸亏细野也算得上强硬“不管怎样,就一起做(音乐)吧。”
才有了教授这一段随意玩玩就不小心成名,而且还不小心成为世界电子乐元老之一的经历吧。
-
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2 ) 《坂本龙一:终曲》海啸、癌症和破钢琴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2011 年 3 月 11 日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 9.0 级的大型地震,这场地震引发了高达到 40 米水墙的海啸,并直接导致了福岛核电站出现了严重的核泄露。

这次三重灾难一共造成了 18,446 人死亡或失踪。此外还有 3,500 人灾后因伤病或自杀而死亡。311大地震对日本社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6 年后受灾地区的房屋虽然重建,但依旧有超过一半的人拒绝返回家园,上千人因为这次冲击患上精神疾病或自杀。

2012 年,坂本龙一出现在了日本东北部宫城县的一所农业高等学校中,他此行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去见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破旧钢琴。
我很好奇,在海啸中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钢琴一旁是有海水浸泡痕迹的白色幕布,白色幕布上有明显的痕迹,表明海水曾经淹没过这里,而钢琴上漆皮胀裂的痕迹,则表明这架钢琴一度在海水中漂浮浸泡,除了断掉几根琴弦以外,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
坂本龙一用这架钢琴的音色采样,完成了之后专辑《async》的部分单曲制作。

《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始于 2012 年的夏天,恰逢福岛核电站重启引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活动,导演Stephen Schible 最初想要拍摄的是坂本龙一参与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以及坂本龙一创作音乐作品的状态,但没想到自此开始发生了更多意料之外的故事。

在陆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的前避难所中,人们围坐在地上,屋内唯一的照明除了出入口的灯光,就只有围住的一台钢琴的几个光柱。人们在等待前来灾区慰问的坂本龙一,从90年代越来越关注日本社会的教授,总会在类似的场合出现。

坂本龙一与观众们打了招呼,请大家“请尽量以最舒服的状态享受音乐”,然后开始与小型弦乐队合奏经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此时的这首歌像是在歌颂树林和阳光,又像是坚实的精神避难所。

不幸的是,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拍摄开始的第三个月,摄制团队和坂本龙一同时得知了他罹患喉癌的消息,当时导演考虑到坂本龙一的恢复疗程,拍摄工作曾一度停摆。
但坂本反而鼓励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工作,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癌症在拍摄期间被发现本身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来讲是一个不可错过重要的戏剧性转折——即使对于自己有些残忍。


坂本龙一的儿子作为一名独立的电影制作人也参与到了拍摄中,很多家中的镜头都来自坂本的儿子。所以在坂本龙一家中的很多拍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摄像师与拍摄对象的关系,还有父亲与儿子的家庭互动,亲情的温度和情绪的自然流露,使得这些片段有了超越纪录片本身的深切含义。

对于罹患癌症的坂本龙一来说,那架被海水浸泡过的钢琴,“像一具死尸”,这是在三重灾难数万人遇难的社会氛围下,一架幸存下来的钢琴给坂本龙一留下的第一印象。但他此时并不忌讳谈生死,也曾乐观的说,这架钢琴发出的声响是来自大自然的调音结果。

这部影片不仅仅记录了坂本龙一有关社会活动、配乐工作和治疗过程的片段,还记录了他在创作和独处过程中深邃而沉静的思考,以及原始的自然音色采样方式,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细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们却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这就是坂本龙一”。


PS.坂本龙一的一段过往
说到社会运动,坂本龙一在学生时代其实就十分热衷,他曾在读大学时前往武满彻(日本著名作曲家,配乐代表作品有黑泽明的《乱》)的表演现场发放反武满彻的小册子,后来与武满彻深谈之后却成为忘年之交,并于 96 年武满彻过世后,在专辑《BTTB》中以一曲《Opus》纪念这位至交。

原文(附带配曲)发布于QQ音乐专栏://y.qq.com/portal/headline/detail.html?zid=1142256

——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
分享是你们给我最棒的打赏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Dreamcatcher文化志」 微信搜索公众号关键词「文化志」
DREAMCATCHER出品 ♬ 搖滾死兔子 & 葉子初 & 王小紫 ♬
3 ) 坂本龙一:活出生命的极致
镜头一:核电站重启后,日本东京首相官邸第一次抗议活动。坂本龙一一身西装,黑框眼镜,语气平和:“我也反对核电站重启,大家不要因为一两座核电站重启了就灰心丧气。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下定决心,坚持到底。”
镜头二:路前高田市立第一中学,前日本海啸避难所。 坂本龙一身穿黑色西装,黑色高领毛衣,发如雪,唏嘘的胡茬,因病略显沙哑的嗓音,谦逊的态度,问好。告诉观众冷的话站起来活动一下也无妨。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坐定,《战场上的圣诞快乐》的主题音乐响起……
镜头三:坂本龙一早餐,切好的水果,有香蕉、奇异果、苹果和可能是梨,一壶茶,清淡。餐后,各式各样的药物一小堆儿,放在一张亚麻手绢上,因为手术,唾液分泌量是常人的70%,吞咽困难。神情平静,无喜无悲。
这三组镜头来自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开篇,三组镜头,勾勒出坂本龙一的三重身份:社会活动家、音乐家、病人。2014年7月,日本著名电影配乐大师坂本龙一确诊咽喉癌,遂中止工作。关于坂本龙一患病和康复的故事,记录在另一部纪录片《坂本龙一的700天》里,而这部纪录片,这记录了他另外两个身份的故事。
坂本龙一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当然就是电影配乐了。而这一切,开始于日本导演大岛渚的那部《战场上的圣诞快乐》。影片拍摄于1983年,导演大岛渚找到坂本龙一出演这部电影,而受宠若惊的坂本龙一则打蛇随棍上,声称如果让我配乐,我就参与演出。好在大岛渚导演答应了,让我们不仅收获了传世金曲,还让我们有幸目睹两位音乐巨人坂本龙一和大卫·鲍伊在银幕上相爱相杀。
这部电影让作为音乐人的坂本龙一声名鹊起。几年以后,他又接到一个演员的工作。在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里出演角色。影片拍摄辗转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纪录片里出现了长影),来到长春之后,一天导演突然说,龙一,你给溥仪在长春“登基”这场戏配一段音乐吧。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1988年坂本龙一凭借《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
到了1990年,坂本龙一参与贝托鲁奇的电影《遮蔽的天空》的配音工作。一天夜里,当乐队都已经准备好录音时,贝托鲁奇突然说,龙一啊,音乐开头的部分我不喜欢,能不能改一改?这个要求让坂本龙一很挠头,他认为这不可能办到,而且四十几个人在那等着呢。贝托鲁奇悠悠地说道:如果是莫里康内,就肯定能做到。坂本龙一吃了这个激将法,他能我也能。
坂本龙一说:“电影配乐工作其实是一项很被动的工作,你要根据导演的要求谱写音乐,并没有很高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因为有了这些条条框框,反而形成了某种挑战,激发了音乐家的灵感和野心。这感觉有点像中国古代诗词里的词牌或曲牌,它们束缚了表达,却也锻炼了表达。
坂本龙一似乎有点灾难体质,总是能亲历某些重大的天灾人祸。比如美国911事件的时候,他就在纽约,甚至从窗户就能看到双子楼。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当然,被震撼的还有整个世界。据坂本龙一回忆,事件爆发七天之后,人们聚集在广场上为死难者祈福,年轻人们唱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现》,坂本龙一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听到音乐声了。
坂本龙一震惊于人类的分歧,在他看来,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本不该有种族之别,然而如今,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此之大。有感于此,他写下了音乐作品《分歧》,这是他提出的问题。之后,他又自己试图给出答案,写下了另外一部作品《只有爱可以化解仇恨》,这是他在集会上看到的标语。或者说,坂本龙一对世界的理解带着艺术家的浪漫气质,但作品却充满了力量。
这样的表达,自然也不会在日本311大海啸上缺席。而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写下过《圣歌》,这是对原子弹这个可怕武器的反思。音乐会上,银幕上反复出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画面,他的话被剪辑成一个词反复播放:死亡。当年,奥本海默在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之后,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对坂本龙一来说,既然有人倾听他的音乐,他就有必要用音乐为这个世界发声。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坂本龙一是音乐家里的知识分子,他被乐迷们亲切地称作“教授”。
度过了这等波澜壮阔的一生之后,如今的坂本龙一回归平静。一场大病似乎让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热衷于电子乐和实验音乐的坂本龙一,对从自然和生活中寻找声音乐此不疲。每当找到难以置信的声音时,他的脸上就会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或许这才是坂本龙一的灵感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在《西西弗神话》里,作家加缪谈到了他的人生观:一个人若想将人生发挥到极致,就要依靠勇气和理性:“前者让他知道,生活不需要祈求笃信宗教,要认识和接受自己;后者让他明白自己的局限。明白自由的有限……以及人之必死,就能在有生之年活出生命的极致。”我觉得,坂本龙一用他的人生践行了加缪的人生观,而为他提供力量的,则是音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能够创作音乐,就感到相当幸福了。”
4 ) 你还能看几次满月?
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
这是北极的某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
“我正在垂钓声音啊”, 他小声说,说完笑了。
他收集着冰川死去时的呻吟。
/
另一个早晨他吞下近十种形态各异的药片,用细细的牙刷反反复复的刷牙。
“生病之后我的抵抗力变得十分脆弱,随时需要保证口腔的卫生。事实上,我后面的牙齿可能已经死掉了”,“我得小心防止复发。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
然后他走进工作间,坐上充气保健球,继续指挥声音的舞蹈。
/
在上周刚结束的Tribeca电影节上,《坂本龙一:终曲》的导演带着它回到曼哈顿下城。
导演说,原本的计划是拍摄一个演奏会电影,没想到开拍的第二年,坂本确诊癌症,全面停工。计划失去方向。最终,连续拍摄了五年的素材剪成一个类传记的纪录片,配合着坂本先生新专辑的创作,变成这部《终曲》。
Tribeca电影节也很特别,它是911后专门成立的电影节,以Tribeca为中心。17年前的那场浩劫的事发地离这里不远,距离坂本先生的工作室也不远。那年听到声响的他立刻拿起相机冲上街头,拍下顷刻间颓然的文明,拍下错愕的行人,但他着重挑出了一张,是从初生的废墟前掠过的鸟——
“它们会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虚弱的人造物和若无其事的自然形成微妙的对立。
几天后他路过联合广场时听见有人弹唱Yesterday,突然意识到音乐已经从生活中缺席了整整一周,而自己竟已觉不出异常。
/
命题从那时就已落定:如何使作为人造物的音乐也获得永恒的可能?
——既描述每个当下的丰富,又咏叹命定的残缺;
——既缝补支离破碎的立场,又对诸此种种一言不发;
——既使用休止符,又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
/
东日本大震灾后,他听闻有一架钢琴扛过了海啸,赶忙上路“朝圣”。钢琴被水泡得太久,琴弦失去张力,琴键松弛在各自的位置如犬牙。他却见得欣喜,如获至宝。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把自然的形态全部按我们的意愿扭曲。这些木头需要年年月月的机器压力才能固定成一架琴的样子。而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说,琴松了,音跑了,需要调琴了。可那其实是,自然正挣扎着回到过去的形态。那跑掉的音,是大自然修复力的鸣响。”
镜头聚焦在钢琴上流转的手与黑白色的琴键;
拉远,继而入镜的是他的黑毛衣和白发,黑白与黑白交响,经过癌症的人与经过海啸的琴共鸣;
再拉远,台下的一排排观众入镜。
你不会预料到那一对一的合唱其实有诸多围观者在场。
他把当下完整的自我交给众人,连带着那份孤独,以及孤独与孤独的共振。
/
再往前是他年轻时的飞扬,例如在拍摄《末代皇帝》时他将钢琴搬上卡车,狂飙在大连、长春、北京的街头,嗅着那古老王朝的遗风,在颠簸的飞车上复刻末代余韵;例如一周写出45首配乐;例如让整个交响乐团等在一边,在20分钟内彻底改写前奏;例如以生涩的演技和David Bowie飙戏,喊卡后再一起回到房间畅聊音乐;例如作为刚开始玩儿电音时试图用自己的手指赶上机器的指令。
直到生命的单向性一再展现在他面前。他才向着那些濒死与永生所发出的声音出走。
他将万物组成乐队,把水桶倒扣在头上站进雨里听雨滴的叩打,去非洲捕捉原始部落舞动的节奏,用小提琴的琴弓拉奏钹,向海螺里送入风,踩在落叶上。他还穿上防辐射衣到福岛隔离区看被射线定居的空城,站在反核游行的前列,把那首《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带给灾民,“大家冷了吧,来听音乐吧”。
/
那个成语叫“冰山一角”,基于“冰山是无比庞大”的假设。
事实上冰川一角也许就是全部的冰川,融解掉就不复存在。
最好再有一个类似的词,给生命。我们站在一个段落望不到边,就总忘了有终点存在的生命。
新专辑一首叫full moon的音乐里,坂本把一段他喜欢的话让人用中文日文英文韩文法文等语言念出来,做成音样,那段话说:
“因为不知道我们何时会死去,我们总以为生命是某种取之不竭的财富,可有些事只发发生那么几回,其实是少数几回。
“你还记得几个你童年的下午,那些无比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们你就也不再是你的下午?也许就只有四五回,也许甚至还不到。
”你还能看几次满月?也许就剩20次。尽管你还以为那将是无尽无穷。“
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我还有多久能在万里狂奔的终点把你找到?我还有多少次,能得到你崭新的礼物,再告诉你我的心情?
全球变暖,冰川消融,
全球变吵,乐者苦笑。
5 ) 坂本龙一:永不终止的终曲
本月初,跨度五年的坂本龙一纪录片电影《Ryuichi Sakamoto: CODA》在日本上映。coda在音乐术语中的意思为一个乐章最后的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日文译名为“最终乐章”,在豆瓣上的中文译名为“终曲”。纪录片主要按照2012年到2017年的时间顺序,中间剪辑了30年前参与末代皇帝等电影以及40年前作为YMO活动的宝贵片段。 一开始是2012年,坂本龙一前往海啸灾区,在那里弹了曾经“溺过水”的钢琴。钢琴发出走调而飘忽无力的声音,“我感受到这是钢琴的尸体”,他说。2014年他又前往福岛灾区(距离地震三年后),穿着防护服接触那里殘败的声音和画面,之后还参与了反对核工程的游行演讲。 /

我特别喜欢这一版的电影海报。这个奇特的画面是这样:在某个下雨天,他打开后院的门放出去一个玻璃缸,想听听它被雨滴击打的声音。过了会儿拿进来敲一敲觉得不太对,又换个塑料桶,这次干脆套在了脑袋上,走进了雨里。雨水淅沥沥地打在他身上,可他毫不在意。追逐声音的时候简直像个小孩。 可他终究还是老了。2014年7月他得了咽喉癌,休养了近一年。期间他虽然想拒绝《荒野猎人》音乐的工作,但因为太喜爱伊纳里多导演,带病坚持作曲和录音。在studio正录着音,他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录音师连忙摘下耳机。平静过后才继续录音。 七八种药丸一颗一颗就着水吞服,之后安静地坐在书桌边吃水果。摘下眼镜也不在工作中的他看着窗外慢吞吞地吃着苹果,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老爷爷。之后他起身准备去刷牙“一定要好好刷牙,我的抵抗力已经变得很差,不过我牙齿后面的肉应该已经死掉了。”白发苍苍他边认真刷着牙边说道。墙上挂着二十代画着夸张的眼影,头发乌黑的坂本龙一肖像。 / 1987年的北京是怎样的?在日本的电影院荧幕上看到我出生前的中国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坂本龙一那时候突然被要求为《末代皇帝》客串一个角色,同时还要作曲。导演给他用卡车运了个钢琴到片场,他只得在片场白天拍戏晚上作曲。影片中剪了几个《末代皇帝》的镜头,八几年的电影放到现在看质感仍是非常好。 / 他对声音本身有着很大的执着。为了寻找自然的“声音”,他前往非洲北极圈等世界各地亲自录音。在一处极寒的地方,他走到高高地冰墙边上,拿出两个小嚓轻轻一碰,立刻飘荡出了清脆而有余韵的声音。他露出惊喜的表情,像个小孩一样咧着嘴笑:“这可真是厉害!” 、“这是混合了水、云朵和大自然的声音”。 之后他蹲在冰面旁,将录音工具用绳子拴住投进裂开的冰面下,直至没入水中。他鼻尖上已经结了小冰珠,抬头看一眼摄像机笑着说:“I’m fishing the sound(我正在钓声音呢)”。 / 在看过坂本教授制作《async》的过程后,再去听这张专辑就又多了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之前我翻译过的杂志对坂本龙一专辑的采访中,也有比较详细地解说了乐曲的构思,但真正看到他工作的画面又是另一番感受。比如你不会知道他其实是坐在健身球上制作音乐;比如终于感受到录andata的阁楼的那架钢琴在空间里的声音;比如利用磁缸共振(手摸磁缸边缘)创作音乐时的魔幻感。 / 这部纪录片电影优秀的地方在于它传达了当时的气氛。 坂本龙一和两位乐手前往灾区临时避难的体育馆,给受灾群众演出。当《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的音乐响起,我突然就觉得鼻头一酸。悄悄抹泪的时候听到后排的观众也纷纷开始吸鼻子。不仅仅是看到灾区的情状,也不仅仅是看到努力的教授,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些遥远的回忆。好的音乐和电影可能就是能够唤醒并永恒地承载人们的感情吧。他作为时代logo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他却说:“无论我们音乐家怎么做,都有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显然他觉得自己仍做得不够多。 / 坂本龙一绝对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又能体现在他对音乐的追求中,继而反馈进他的音乐里。 在如今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审丑为乐、浮躁和欲望甚嚣尘上的世界里,还有一位老人怀着纯粹的感情去聆听声音(社会的声音、自然的声音),创作音乐,是多么让人慰藉的事情。到底,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坏。 “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或许是十年五年,或许是一年,我只希望我在活着的时候尽可能再多做一些不让我自己羞愧的音乐。尽可能多留下一些音乐在这个世界上。”——坂本龙一
<严禁任何形式的演绎、复制及转载>

6 ) 这部历时五年的纪录片,带你走近最真实的坂本龙一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坂本龙一前往受灾地区,听闻有一架钢琴从海啸中死里逃生。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钢琴浮到了海水上方,退潮后,居然神奇地完整保留下来。
坂本龙一走上前,指尖触碰琴键发出沉闷潮湿的声响,他说,那一刻“犹如在钢琴的遗体上弹奏”。

日本“新音乐教父”坂本龙一在音乐路上走了四十多年,电影制作人Stephen Nomura Schible经过五年酝酿,终于完成纪录片《坂本龙一:CODA》,最近影片则在港上映。开头描绘的一幕,正是这部纪录片的开场故事。
多年来,坂本龙一始终积极参与环保、和平活动,关注社会事务。“311”福岛核灾令日本损失惨重,其后政府决定重启核电站,东京民众集会抗议,坂本龙一也亲临支持。他在简陋的小房间里,重新弹起1983年为大岛渚电影《俘虏》所作的主题配乐,此情此景下,这首曲子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即使身为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对“人类制造的音乐”,也有过怀疑。他说钢琴的“走音”,其实是来自自然的树木试图回到原始状态的结果,所谓“正确的音”,只存在于人类概念里。而“911”事件时身处纽约的经历,让他发现,在面对巨大的灾难和冲击时,过往如影随形的音乐在城中消失了一周的时间,竟然都无人觉察。他猜测:或许在非和平的状态下,人类会自然地抗拒音乐。
相比而言,自然的声音淳朴而透彻,坂本龙一也孜孜不倦记录着这些转瞬即逝的声响。下着大雨的天气,他把巨大的玻璃罐放在雨中,试图录下雨点敲击玻璃的噼啪声。过一阵子后他拿回罐子检测成果:“罐子太厚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找出一个薄薄的铁桶,这次索性将桶顶在自己的头上就走进了雨里。

他曾受邀前往北极,但去看的却不是当地的动物,而是冰融化成水的状态。坂本龙一甚至玩起了“钓鱼”:“我在钓声音”。那一瞬间,这位音乐人的眼里是有光的。

近年对自然声音的执念,还与他2014年被医师诊断为咽喉癌有关。低烧、吞咽困难,这些都在影响坂本龙一的工作状态。于是二十多岁入行就从没停下来的坂本龙一,第一次获得了休息的机会。但他想得透彻:希望随时走都不感到遗憾。那些之前没有采集到的声音,过往没有尝试过的事,没有合作过的人,都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在病重状况下坚持每日工作八小时,完成《神鬼猎人》的配乐,便是因为“欣赏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作品”。
影片中还包括坂本龙一事业中的众多“大事纪”,如他1983年在《俘虏》中的出演及小试牛刀,《末代皇帝》从负责溥仪登基一幕的音乐到全面操刀,在《The Sheltering Sky》中用30分钟重写配乐的趣事,甚至还有他在合成器摇滚乐队“黄色魔术交响乐团(YMO)”中任乐手的片段,他在当中,认真演示了何谓“人手弹奏怎样都快不过电脑”。

从对各式物品敲敲打打,开始编排,到这些声音片段成为作品里的功臣,坂本龙一的生活片段和这些作品在电影中以一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方式,行云流水地穿插在一起。纪录片名中的“CODA”意为“乐曲尾声的终曲”,亦是坂本龙一在1983年出版的精选专辑名。而坂本在片中为其赋予新的含义:“一曲的终结,代表新乐曲的开始”。

“要多动动手指(弹琴)才行啊”,影片的结尾,今年66岁的坂本笑着说。而属于他的新乐曲,还有时间慢慢完成。
原文刊于橙新闻:http://www.orangenews.hk/culture/system/2018/05/02/010088331.shtml
微信公众号:苏西与老丸的点心铺(dimsumdi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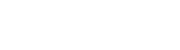




















下咽困难的吃治疗癌症的药,末代皇帝的自拍花絮,出席游行去福岛灾区,熟悉配乐的现场演奏,在居所鼓捣不同的乐器,911当天在纽约拍摄的照片,捧着塔可夫斯基拍立得的书要做出自己的飞向太空,去非洲北极寻找原始纯净之音,对永恒之声的追求,几次背身之影,音乐使人自由,期待教授身体健康以及新作品和本片之续。北影节天幕云彩,资料馆与异步二刷。
不喜欢剪辑 但音乐可以拯救一切
北京这场该死的雨让人心绪烦躁,但当海报那一幕出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伟大的艺术家不会只着眼自己的创作,而总是心怀高远的。感谢坂本,感谢音乐。ps,末代皇帝也是在天幕看的,算是一种缘分吧,而且也是我最爱的坂本之作了。还是感谢。连来带去历时六小时的路程,60站车,坂本!我对得起你惹!@天幕
少年老了应该有的样子
他说,我想把融雪的声音钓上来。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坂本龙一就坐在正后方,第一幕演奏劳伦斯乐曲的时候湿了眼眶。干嘛要评价那么多片子的好与坏呢,爱这个人和他的音乐就够了不是吗?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亚洲人的骄傲吧。
魅力超标,隔着银幕源源不断地辐射出来。仙子老了也是仙子,指甲剪得短短,手指上也不长奇怪的毛,鬓角三十年如一日修得利落至极,后颈也是光滑洁净的,头发随手一拢就乱得恰到好处,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洁净感,我好像是第一次看着一个六十岁以上的男性想:“嗯,他身上一定很香……”看身形挺拔得就像二十多岁的青年,处事时又有中年人的成熟和余裕,浑身上下还充满了少年人才有的对世界的好奇心,谈起会让人惊呼“这还是人吗”的年轻时的壮举,也是一副回忆学生时代社团趣事的口吻,妈的,除了一声“仙子”我还能称呼您什么!
3.5 纪录片本身实在是太soso了。但教授魅力摆在这,全程鸡皮疙瘩🙃
他用尽一生去探寻音乐的意义,爱护这个世界,拥抱着大自然,他喜欢弹奏巴赫的乐曲,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对于埃尼奥莫里康内表示不服,即使在休养期间也要挑战《荒野猎人》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坂本龙一的音乐就是他的人生、他的感受、他记录的自然语言。这些年不论是《南汉山城》OST中的凉风刺骨,还是《怒》中的深情与绝望,都是真实的,这是坂本龙一的力量,音乐的力量,艺术的力量,他就是那一架被自然调过音的钢琴。
没想到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对坂本龙一如此有影响。《末代皇帝》拍摄和作曲花絮难能可贵,还提及贝托鲁奇在拍摄遮蔽的天空时威胁再不让他满意就换人,莫里康内也一样
开始还在说癌症问题,后来就不再提了…但对于创作经历的梳理还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家真正贴近自然的时刻,是他放弃叙述和模仿环境的时刻。对海啸钢琴的思考太棒了。飞向太空出来的那一段泪崩。事实上坂本龙一在不断观看塔可夫斯基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塔氏对种种意象的呈现恰恰是去符号化的,是没有阐释余地的,是一种纯净的混合。诗就是这么有趣神秘。
如此厚重的人物,导演未免把素材组织的太过于随便了。
Merry Christmas M Laurence 的第一个音符出来的时候整个眼泪都往眼眶涌了。看到坂本龙一真人确实非常可爱。
坂本龙一真是一个温和、谦逊、善良同时才华光芒万丈的人。为了治疗癌症,他停下从未停止的工作,忍着疼痛每天吃很多药,只为“在世界多留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如果不努力多活几年我会很遗憾”。像孩子一样到处记录声音,听见喜欢的发出由衷的赞叹。纽约的灵魂被他捕捉到了,爱教授❤️祝愿健康长寿!
永恒的音符就是大自然的声音,面对生命的衰竭亦是如此。
“大家很冷吧,请欣赏音乐吧。”今晚,六本木,几次泪目。
TIFF放映,历时五年的纪录片,覆盖了教授大多数配乐名作和近期重要事件,911,反核运动,async制作,当然还有咽癌。教授本人映前挨拶,比纪录片里清瘦很多,手边专门一瓶水。行为举止像个小男孩,非常可爱。监督会说日文,态度很谦逊。
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配乐大师,也是反战反核的环保人士;从911的纽约到人类源头的非洲,从福岛到极地,一直在创作,从未想停歇。真的很想采访坂本龙一:请问几十年如一日的帅是什么感觉?福岛集会弹奏的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啊顿时我就泪目了~~~
片子本身不能说多好,但坂本龙一太令人钦佩了。”你还能看几次满月?也许就剩20次。尽管你还以为那将是无尽无穷。“
从纪录片的角度看并不算出色,不过本人的魅力实在太闪耀,比较触动我的是教授谈塔可夫斯基和Solaris的段落。